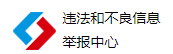朱利勇的竹根雕作品。
在江北区新马路的烟火褶皱里,青山竹木文化馆静静伫立。午后的阳光漫过中式短褂,朱利勇弓身伏在旧木工作台前,左手攥紧形态苍劲的毛竹根,右手木槌与凿刀相撞,“笃”声震落棕黄竹屑。这一方天地,藏着他以刀为笔,在竹根上书写人间烟火的故事。
朱利勇,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、中国民间雕刻艺术大师、竹根雕非遗传承人。作为竹根雕行业“领军人”之一,他在4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留下不少经典作品,其中《鼓乐小虎队》荣获中国工艺美术最高奖“百花奖”,《二泉映月》《悠悠茶韵》《变天记》等几十件作品荣获国家级和省级的金奖和银奖。
1
竹海学艺,刀笔锋芒初露
1965年,朱利勇出生在象山西周镇竹海深处的一个小山村。童年的他,常看父辈与竹周旋,却未料到,1981年那个夏天,命运会将他推上竹根雕之路。因绘画天赋被老师傅相中,17岁的他成了竹根雕学徒。
两年学艺时光,朱利勇像扎根竹壤的笋,汲取着雕刻技艺的养分。出师时,他已能循着竹纹,让打坯刀、圆刀、三角刀在竹根上共舞,雕出初显神韵的作品。
“竹根雕不像木雕那样四平八稳,它的灵魂藏在天然的疤结和扭曲的根须里。”朱利勇摩挲着一块带瘤节的毛竹根,记忆回到在竹林深处的寻根时光。
“五年以上的毛竹根才能入眼,须得质地细腻、纹理清晰,最好还带着自然形成的弯折。”在他看来,竹根雕创作“七分天然三分雕”。

朱利勇在雕刻竹根雕。
2
刀光竹影里的坚守与突破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象山竹根雕外贸红火,远销20多个国家,朱利勇也在这股浪潮中创办了自己的雕刻厂。但短短几年间,产业快速扩张,一些问题逐渐显现:竹根雕产品的质量大幅下降,市场开始出现滞销现象。
不少竹根雕企业陆续倒闭或转产,朱利勇也没能躲过。1994年工厂倒闭时,望着仓库里堆积如山的半成品,他没有沮丧,相信只有如竹子般坚守初心,“守得住寂寞,才能在竹根上雕琢出美的艺术。”
蛰伏半年后,朱利勇重拾刻刀。为了获得生活体验,创作出好的作品,他几乎到了“疯狂”的状态,不仅研究各种人物的神态,为了捕捉失去亲人的人们面部的表情,甚至去了殡仪馆。零下2℃的半夜,突然来了灵感,下一秒他会出现在工作室,把脑海中的想象凝于竹根。
就是在这日复一日的观察和雕刻中,朱利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作品风格。他的代表作品《变形记》,就以略加变形的卡通艺术手法,利用极有限的竹根原料,巧妙刻画出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:晚清大臣眉头紧锁,似乎在密谋着什么;地主看到留洋归来的儿子,神气十足;帮会头目则伺机重整旗鼓,心中盘算着如何发财。
2022年,江北区新马路的清代洋房王宅,成了他新的“竹艺舞台”。改建的青山竹木文化馆里,陈列着朱利勇近年来呕心沥血的作品,包括单个的人物肖像、描绘社会关系的群组雕塑,以及展现山水风情的根雕。它们共同的特点是采用幽默夸张的手法,生动地再现了生活场景,使得人物形象栩栩如生,充满趣味。
“我们要把每一件竹根雕,从工艺品努力提升到艺术品的高度,那就坚决不能做普通大路货,不要想着靠模仿抄袭去投机取巧。”朱利勇坚信,真正的创作应该是随心所欲的,看到竹根的材料,想象它像什么,就创作什么。“这就是为什么竹根雕作品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,你永远找不到两件完全相同的竹根雕。”
3
新马路边的传承之窗
清晨5点,新马路还裹着静谧,朱利勇的刻刀已开始“苏醒”。工作室的窗对着老街,常常吸引路人驻足观看:只见他先用大平刀铲去须茬,再以圆刀勾勒眉眼,最后用三角刀刻出衣褶的阴影,竹屑在晨光中飞舞,渐渐露出一个咧嘴笑的卖货郎。
这一幕,让竹根雕的烟火气传播得更远。这也正是他把工作室设在临街的初衷:竹根雕不能束之高阁,要让人们看见它诞生的过程,让雕刻成为活态展示。
“竹根雕要传承下去,不能只是说说,如果大家只做研究,而不动手去做,这门手艺是留不住的。”在青山竹木文化馆里,总回荡着朱利勇对学员们如此这般的提醒。他还在馆内开设体验区,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技艺,耐心地指导每一个对竹根雕感兴趣的人。他说,“非遗传承不是复制,而是点燃兴趣的火种。”
儿子朱峰也接过接力棒,从大学开始就沿着父亲的足迹一步步学习雕刻,还在线上推广竹根雕,普及竹根雕这门艺术,让更多年轻人知晓。作为江北区外滩街道新马社区的文化特派员,朱峰正与父亲朱利勇筹划将外滩文化融入创作,让传统技艺与现代记忆碰撞出火花。
暮色漫入工作室,朱利勇收拾刻刀。这些伴随他多年的工具,刀刃发亮、木柄留温。窗外新马路华灯初上,他的影子与竹根雕里的百态人生重叠。案头未竟的竹根,等待着下一刀,继续在刀光竹影间,讲述人间烟火的传承故事。
来源:宁波晚报